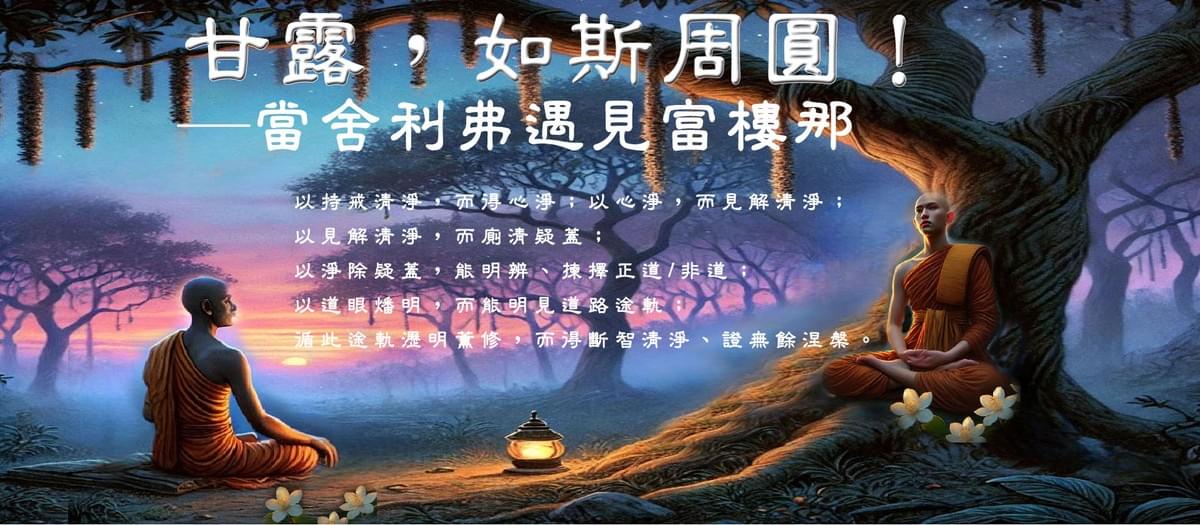
AI製圖:Nicole Liang
甘露,如斯周圓!
──當舍利弗遇見富樓那(註一)
梁寒衣
如果「智慧第一」舍利弗與「說法第一」富樓那相逢,那會是什麼情景?
是議論風發,黠智如潮,無量璀璨的珠璣、哲睿的思辯皆撞擊、迸裂而出,凝為法的風雷與海嘯嗎?
答案是:他們從未相逢過!──縱使經過悠漫的修行,二人俱已證入高峯,也皆具德譽與聲名;尤其恒為如來左右的舍利弗更有「第二尊佛」之稱(註二)……然則,即若修驗的歲月如許遼長,二人卻宛若睽隔一方,各俱專注於自我深密的觀修與弘化中,未曾見過、也未曾識得彼此。
乍看不可思議,而真實即是如此,二人的初相逢,形成了探討法義的周延、完滿性的〈七車經〉(註三),此七車,為修法者及弘法者均須於修道的途軌中慎明、遵循的修法次第,不得錯亂顛倒、或漏失遺忘。

攝影:哈克
經卷的記載是這樣的:
彼時,世尊與諸大弟子結夏於摩揭陀國王舍城的竹林精舍;而尊者富樓那亦於出生地──於故鄉迦毘羅衛國(註四)與僧侶們共同結夏。結夏完滿,僧侶們乃自迦毘羅衛國啟程前往王舍城朝覲世尊。
「君自故鄉來,應知故鄉事」──如來關切著遙迢鄉關的僧侶們修持的狀況,和煖垂詢道:「於我母土,何等修行者具足下列條件,足以為其他道者的典範、為修法者所讚歎效學?
一、自身知足、少欲,亦稱揚知足、少欲之益。
二、自閑居寂靜,亦稱揚安處闃寂、靜處觀修之必要。
三、自精進不懈,亦稱美精進之於修持的不可或缺;緣於一切道法,諸善福德俱由之而生。
四、自攝持正念,亦稱述正念不失,為道者須隨時警醒、返觀自身的正念。
五、自恒住一心、禪定三昧,亦稱揚住持一心、襌定不亂的修習。
六、自智慧明睿,亦稱揚智慧明睿。
七、自漏盡解脫,亦闡揚無漏解脫之聖道。
八、自渴仰如來、勸發菩提、成就歡喜,亦不捨有情,恒恒勸發渴仰、成就歡喜、廣植菩提;了知此為法芽法苗生起的根本。
──箇中,誰能具足?誰為典則?」
「富樓那!──尊者富樓那具足世尊舉揚的一切,堪為大眾的典範與法式!」母土比丘異口同聲地回答。
於時,舍利弗亦在眾會中,他默然聆聽著比丘們的讚歎,油然昇起之於富樓那的慕往。稍後,世尊起身回歸拘薩羅國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,舍利弗仍盤桓於竹林精舍與來自如來家鄉的比丘們共處了些時日,彼我議論道法,於比丘們的稱述間更更昇起之於富樓那的嚮慕。「那是生命中合該相晤的道人!」舍利弗胸中決定。
懸念世尊、慕渴深切,此際,富樓那也自迦毘羅衛跋涉來到了袛樹給孤獨園。當舍利弗與母土比丘們抵達,富樓那正置身於一眾比丘間,專致聆聞如來說法。
「眾中哪一位為尊者富樓那?」隔著講堂窗口,舍利弗低低問母土比丘。
「趺坐於如來跟前,顏面白皙,鼻端高聳如鸚鵡的,便是尊者富樓那!」比丘亦低聲回答。
次日黎明,富樓那入於舍衛城乞食,而後踅入安陀林中,於一樹下結跏趺坐。舍利弗亦默然跟隨,如彼一般,入於舍衛城乞食,足音靜靜,隨著那名皙潔的身影一併入於安陀林中,於一樹下結跏趺坐,就在距離富樓那不遠之處。
二人寂然趺坐,及至流霞張滿天際,舍利弗禪定而起,行向富樓那,作禮問訊道:「賢者,可是追隨如來修習梵行?」
回答:「如是。」
「是因持戒清淨而追隨如來修習梵行嗎?」
答言:「否也。」
舍利弗胸中詫異,於是更提出以下六問請教:
一、是因攝心清淨而追隨如來修學嗎?
二、是因見解清淨而追隨如來嗎?
三、是因能徹底淨除疑蓋嗎?
四、是因「道」與「非道」知見明白、能善分辨抉擇嗎?
五、是因道跡分明,能掌握修行的途軌與路標嗎?
六、是因依此道跡、循此途軌而修,而取得最終的「斷智」(即阿羅漢斷除「貪嗔癡」三結,獲得解脫)清淨嗎?
富樓那均寧然答言:「否!」
舍利弗詫異非常!富樓那的回答違拗了向所行來的認知。一己正是因此而證聖智聖道的啊!何以富樓那均答為「否」?
「那麼,是因了什麼、為著什麼而追隨如來呢?」他更啟問。
「是為著無餘涅槃。」(按:無餘涅樂,指阿羅漢斷除「貪、嗔、癡」三結,永不再墮入三界輪迴。有餘涅槃,指羅漢們尚未圓寂前、還留著最後的肉身。)
舍利弗就更不解了!
「然則,方才我問,是否因持戒清淨而得無餘涅槃,以及是否因攝心清淨,淨除疑蓋……乃至道眼明白、燔明途軌、循軌而修而取涅槃,賢者均答為『否』,是什麼緣故?」
「緣於若以持戒清淨,如來施設無餘涅槃之道,則是以偏概全,以有餘稱述無餘,以不究竟的稱述究竟的;其餘六種亦然。賢者!若離於以上七者,如來可取無餘涅槃,則凡夫亦可取無餘涅槃,唯因凡夫一向恒離於此七者。」(按:有餘,即「還有剩餘」,有未竟、未了;為不了義。無餘,即究竟、圓滿,為了義。)
「正如拘薩羅國的波斯匿王因有事,須於一日之內抵達婆雞帝市。王於是思惟:快捷之道,莫如於兩城之間,沿驛布置七車。從舍衛城出發,到第一驛,捨第一輛車、轉第二輛;而後至第二驛,再捨第二輛,轉乘第三;於第三驛,更捨第三車,轉乘第四……如斯,第五、第六、第七;以七車的迅捷轉乘,即可於一日之際抵赴婆雞帝。」
「因之,若群臣問起:王是否乘第一車而抵雞婆帝市?王則回答:否!其餘數車亦然。──正確的描述應如以上:是搭了第一車,後捨第一車,轉第二車……輾轉乘至第七,始於一日抵定。」
「如是,此修法的道次第亦然,任答一種皆非,皆為有漏、有餘。正確的詮述應為:
以持戒清淨,而得心淨;以心淨,而見解清淨;以見解清淨,而廁清疑蓋;以淨除疑蓋,能明辨、揀擇正道/非道;以道眼燔明,而能明見道路途軌;循此途軌瀝明薰修,而得斷智清淨、證無餘涅槃。」
「此才是圓融無漏的修法、詮法次第啊!」舍利弗呀然稱嘆、滿面光輝:「賢者姓名為何?如何稱呼?」
「我名富樓那。名『滿』,從母姓『慈』,可呼我滿慈子!」
「賢者滿慈子智辯聰敏、圓融無礙,能自作證成就甘露界,亦能高樹甘露法幢,敘說甚深法義,安穩利益有情!所有淨修梵行的佛子均應隨時往見,攝衣禮拜,能得大利!我亦如是,願恒時見,攝衣禮拜,為得大利──」舍利弗法悅充滿、由衷讚歎。
「賢者名何?如何敬稱?」富樓那謙然微笑,反問道。
「我名舍利弗。從於母姓『舍利』,亦可呼我鶖鷺子!」
謙和的微笑再度綻開於富樓那白皙的顏面,如垂枝茉莉的皎然綻放:「我今竟與『第二尊』共論而不知!與如來法將共論而不知!與善轉法輪、善轉弟子、智慧圓湛的尊者共論而不知!」富樓那驚詫而歎悅歡然:「倘然知是您!──智慧灼皎,第一、最勝的舍利弗,我必不能張口!尊者才是成就甘露界,能深究、深問甚深法義之人!一切梵行者均應時時往見、頂戴啟問、定得大利──我亦如是,願恒時會晤、恒時頂戴!」
晚霞墜落下來,安陀林的昏色靜靜,空氣中唯充滿無形的垂枝茉莉,盈盈、芬芳、而皎素。晚風拂動著衣衫,二尊者的形影如碑,鐫刻入〈七車經〉中──這即是「智慧第一」舍利弗與「說法第一」富樓那的初相逢──一無「兩刃交鋒」的劍客相拄,也無想像的雄辯與激智,唯有無盡的虛懷,精確精嚴的法義刻銘,還有無限的孺慕、欽仰,與歡喜讚歎。
結夏已過,猶存的夏螢自林間草隙間昇起,一隻隻,如追尋的眼;一盞盞,亦如燃燈、提照的眼。而兩位燃燈人佇立那裡,隔著兩千餘年,我仍看到那無比謙遜謙虛中,智慧道證之所從生,之所以周延、安善、無瑕……
一個不為襲奪的本初純真之心──只為法來,不為競較與諍勝的「純一為法」之心;一切的顏面、聲名、頭銜於茲忘我無存。

攝影:蘇仁浩
「七車譬喻」為修法者不可忘忽的道次第,也是為道者循法而修的標刻與量尺。
重新書寫、詮釋這篇人人可能嫌其枯燥無味、而怠於參讀的〈七車經〉,為著它無垠的謙虛與「無我」:聲名昭著,號為「第二尊佛」的舍利弗,竟如青年時初遇阿說示尊者、皈命佛陀之際一般,默然尾隨富樓那,如彼一般,托缽,乞食,樹下趺坐……以最沈靜、緩慢的鐘擺,擦去顏面、擦去名銜(他可是如來座下智黠炯照、至為深沈浩瀚的喔!)向前乞法。時光、勝名與成就,俱未能改變其本然初度。
兩人皆一樣「以法先行」,擦去姓名,合掌恭敬,先啟法義。
然,這即是「智慧第一」與「說法第一」的真相、真顏──正唯其虛懷無量,能擦滅「我」、擦滅世間一切尊嚴、臉子、虛名,以致能廣涵納、廣開展、廣修學,由是智境無涯、法義辭辯圓湛圓融……這即是無止增上、增明的奧秘。
相較當代,智不足、精進不具,而傲慢自高,而不修不學、牴牾競諍、夷毀凌踏的諸般相狀,灼然是一個值得反思反省的碑石。
當然,打從一開始如來所揭舉的八項行者於日常生命中須安處具足的準則,便不可潦草忽略,須定格檢視(不可最末流變、下墮為,自不精進,也告訴他人:人生海海,不必太用功!結點善緣,日子照常過便好。自不禪定內觀,也四處宣稱:空空坐著,只是浪費時間,何必和自己過不去!自不發菩提心,也怯懦退縮,從不勸發菩提心。……如是一切全相反脫鈎,徒成「名字佛弟子」)。而富樓那以七車譬喻的修法圓融次第,不止是修法者須認真檢視、反觀的行則,也是為道者循法而修的標刻與量尺──它不是大/小乘、顯/密、禪/教的問題,而是要如實薰修,便須循此七個次第、七個路標篤實前進,不能躐等。它們是佛子明澈簡淨、不失法本的「共」法(通常,修法者之難能進益,也即在二、三車、四車「依淨心,建立見解,廁清疑蓋」上,即嘎然卡住;唯因於此雜染器世,能正心誠意、以清淨心求法已屬不易)。
欲修善,便得自最簡樸的模版、典範,老實操作起:謙虛是!頂戴是!七車的每一車,不錯漏,老實搭乘、老實到站是!
單看,給孤獨園的一日,僅是安謐安詳地流過,二尊者縱然已證阿羅漢,依然一無放捨、回歸樹下、安住禪坐;典範如斯,聖弟子便該知所著眼、知所調御了!
寫于二〇二四年五月七日
(註一)參見中阿含第九〈七車經〉(七法品)。
(註二)於南傳佛法,作為佛陀上首弟子的舍利弗,智慧浩深,一向被視為「第二尊佛」。
(註三)七車經,另一譯名為「七車譬喻經」。
(註四)經文僅用「生地」描述,並未指稱出明確地點。然,此「生地」應指佛陀出生地迦毘羅衛國,據稱富樓那也即迦毘羅衛國人,故兩者出生之地,其故鄉、母土如一。富樓那既得法,則返歸迦毘羅衛,於家鄉中修習。
相關連結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