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AI繪圖:Nicole
玄浩誌:
無論現象界何其凋殘,每至除夕,作為禪宗道場,大鑑總會刊出「宗門之眼/祖師禪」的作品,以作為禪和子助鼓。今年恰逢馬年,人們恒常以「駿馬奔騰」彼此祝賀。然,就修法,不蠲除「惡馬八態」,則難能成為一匹良馬;倘連良馬皆不是,就遑論能為駿馬了!
〈惡馬八態〉與〈良馬八態〉為原始《雜阿含經》的教法,也是佛陀最古老的教法──新的一年,我們便以一月為期,刊登〈惡馬八態〉〈良馬八態〉,回歸世尊至為古樸親切的教法。願佛子們能識得此深深意,循此八態立定腳步,老實檢視,誠直觀修……掂一掂、秤一秤,漫長行來自我的修行品質和體氣。
唯能「以法為量尺」,徹底清明、拔除自我修行的病灶與坑陷,始能不負本願,轉進與轉身。
「作一匹如來法道中的良馬、駿馬,乃至千里馬!」──這即是馬年殊特的祝福。
馬之冥想,之二
──惡馬八態
梁寒衣
王舍城的馬墟馬市遠近馳名,相馬者,買馬、賣馬者,以及看客、逛遊者一時雲集。集市鬧熱如潮,人面穿梭如魚,那些光華壯碩、或驍傲不馴、乃至凋萎摧殘、羸形瘦體的馬兒們……凡殊特殊異的,總能吸引目光,令人佇足圍觀、評議紛紛;自然,那些點綴其間光華光煬的貴客、名紳淑女也不例外,令人忍不住投諸目光、而艷羨漣漪。秉守戒律,比丘們托缽乞食行過墟市,固不敢大膽望視光煬光采的人臉,然則,之於那些光煬光采的駿馬,甚或梟傲拔鋭、衰凋摧殘的……亦忍不住如常人般停下腳步,癡癡張望,癡癡看想、思慮。
誰教馬市馬集便是現前風景,便是托缽行腳的日常!僧侶們並非盲人聾漢,怎可能經年經久托缽而不見、不聞?
這個午後,世尊忽然鳴鐘集眾,要談一談相馬術、選馬術。僧侶們一時沸騰起來,俱如奔馬一般興奮來集了!
哦,世尊懂得他們,瞭望見他們心之所好、所想、所求問了!
迦蘭陀竹園的竹葉碧浥青青如永不散的春日,於是,佛陀侃侃談起了祂的馬經。

攝影:梁寒衣
「惡馬,不同於駑馬。無論乍看何其壯碩驃美,宛若優良,並無異狀;世間卻有八種不可親、不可近,難以調教、亦難以御使、任用的惡馬──愛馬者不可錯看、錯認!」世尊的「辨馬術」一鳴驚人,比丘們不禁豎起神經、傾耳聆聽。
「世間惡馬一共有八種樣態:
第一種惡馬,於臨駕車之際,後腳蹋人,前腳跪地,猛揚頭咬人。人中亦有如斯惡馬──若修學者面對善知識或其他同學、梵行者舉發過患過失,提出質疑,則頓生嗔恚,反唇相譏、怒罵道:你這人愚癡無智、不辨是非、不良不善!他明明在揭舉你,你幹嘛攀扯、拉搭我?……態勢恰如第一惡馬的後腳雙舉、踢蹋於人,前腳頑跪於地、拒絕起身,乃至折斷韁繩、馬軛(註一)。
第二種惡馬,則於駕車就位之際,低頭嘶吼、搖振、拔抗車軛。人中亦有如斯惡馬,恰若修學者面對善知識,或其他同學、梵行者舉發過患,提出質疑,則反與揭發者對抗,舉出對方罪失過謬,樣態恰若第二惡馬的怒抗頸項、折斷車軛。
第三種惡馬,則駕車行駛之際,自顧自的、只聽自己,另走他道、义道而去,或復偏車傾斜,使車翻覆。人中惡馬亦復如是,一旦面對善知識,或其他梵行、修學者舉發過患過漏,提出疑點;則不正面面對、回答,反而東說西說、南拉北扯、另說別事、迴避問題;嗔恨、憍慢、隱覆、嫌恨、不忍,使人無以導規、亦無可奈何!恰若第三惡馬的不循正途正軌,使車翻轉、翻覆。
第四種惡馬,則於駕車之際,昂舉頭部、拒絕行進。人中惡馬亦復如是,於面臨善知識、梵行者揭舉過患錯失,請他反觀、回憶時,反抗聲道:我就是不憶念、也不想回觀回溯什麼!……如此牴牾不休、頑抗不伏,恰若第四惡馬的退縮退後、抵抗前行。

AI繪圖:Nicole
第五種惡馬,則於駕車行進之際,但凡給予小小的鞭杖、稍加調御,則扯斷韁繩、折斷馬軛、縱橫馳走。人中惡馬亦復如是,面向揭舉過患錯失,表現出輕蔑、不屑,既不顧念對方、亦不顧念教團,只縱恣自我、自行攝衣持缽、隨意離去;恰若第五惡馬、加以鞭杖,則縱橫馳走、率意狂野。
第六種惡馬,則於駕車之際,高舉前腳雙足,作出像人站立的樣子。人中惡馬亦復如是,面向揭舉、質疑,而傲慢自負,高高踞坐床座,與諸上座大德、修行者共為爭諍理論、駁辯是非、曲直、高下。恰若第六惡馬的高舉前足、仿人站立。不知尊重尊敬,亦不禮讓前輩前賢。
第七種惡馬,則於駕車之際,加以鞭杖、而兀然不動。人中惡馬亦復以是,面向揭舉、質疑,默然不應、悶不吭聲,以巨大的空白、沈默,惱亂、磨碾、凌遲大眾;恰若第七惡馬的加以鞭杖、兀然不動,如木樁般地杵著、形成對峙與磨難。
第八種惡馬,則於駕車之際,盤踞四腳,伏地不起、不行。人中惡馬亦復如是,面向揭舉、質疑,則甘脆自動捨戒,自生退沒、退轉,拋下一切,走至寺門、道場外,放話道:你們可以不說了吧?高興了、滿意了、放心了吧?我現在就捨戒退沒,從此兩不相干、不必說教了!──自暴自棄、不修不調、索性『不幹了!』,態勢恰若惡馬的綣盤四肢、伏地不動、寧賴泥淖。」
「修習聖道的聖弟子啊,不要僅看到外在的馬,須知如來法教中亦有八種難以對治,難以惓革、調伏的惡馬,大丈夫須如實認知、如實拔除。」如來靜靜結語。
迦蘭陀竹園的竹葉如碧綠的眸眼荼亮於比丘們心底。
「良馬見鞭影而行」──那極端聰敏的,早於世尊敘說「第一惡馬」之時,即已洞察世尊意不在馬,唯在以馬為喻、揭剖修法者的種種病相病灶、以及各種反應──尤其在面對常人必有的過失、過犯以及錯誤、錯漏時。人們為修善、修行而來,卻不願、也不肯面向過患錯誤,這不是很大的矛盾嗎?──倘不知坑漥坑洞何處?又如何談修護、填補?不是永墮陷、墜入同一坑漥坑坎間嗎?
即或中庸、平凡的,於世尊舉至「第四、第五惡馬」之際,亦感到心頭的刺痛與不安了。世尊的鞭杖恰似雨點敲打在脊樑上──哦,世尊的「相馬術」指涉著僧團和僧侶們……一匹匹惡馬隨著世尊的描述照妖鏡般的現形現影……我們,究底以惡馬之姿頑強地忤觸、對抗過多少回了呢?
縱使如此,僧侶們仍好奇地想聽下去,世尊的辨馬術的確別出心裁、引人入勝,比丘走在街市、道路,的確見過世尊所列舉的惡馬態勢、以及主人惱苦的情表,直是活靈活現、栩栩如生!……在這裡、那裡,他們都相逢、照見過。
縱若最最鈍漠、頑戾的,也於「第七、第八惡馬」的牴突潑賴中發現、明白了自己。有一刹那間,他們的確想衝出講堂,直截渲洩內在的不快和咬嚙;另一刹那,天生反骨的傲慢與自恃卻也令他們止住腳步、避免立即坐實惡馬的姿態。「看你還能說什麼、扯什麼!」何況,他們的確好奇佛陀所說──世尊究底要狀形狀色、「指桑罵槐」、數落、比喻到何種程度呢?
「我是嗎?我是嗎?」偶有風起,迦蘭陀的長竹則竿竿喁語、淅響如雨。那之後的無數黎明、無數午後與向晚,那些自覺的梵行者們總不住反思、自問──問著、盤整著,反觀、點校著自我胸中的惡馬……一己究底豢養了多少匹、多少時候?又具足了幾種樣態?
於行腳中走過街市,看到狂馬長唳著、掀翻車輛,或踢蹋主人,乃或杵立不動、一步也不肯前行……世尊之於惡馬的描摩仍會應情應景怦然映現……宛如鬼針草般地扎之不去、微帶痛感。
「我是嗎?我是嗎?是嗎?是嗎???……」隔著二千五百年,聲音仍一徧徧擊叩胸茨──初參《雜阿含經》,初見「惡馬八態」的撞擊,迄今仍穿徹肌骨、沒齒難忘。「惡馬八態」是一見、即永誌不移、並不須反復記誦的教典。自茲,發誓永不為佛前惡馬。
須反復進行的,卻是一徧徧的省觀和對照──看看是否具足八種惡馬的任一樣相?究底具足幾種?其過患輕重、大小究底具足幾分?──認為此教法是「初、中、後善」的,修行者若不想空廢此生,則始自初基修行、終至末後結案,都須恒為警愓,恒為參佐、省思。「不成為任一樣態的惡馬」是起行修學根本的心態與基礎。要進益,便得志決斷捨。
唯因所謂「惡馬」並非八態具足才堪稱惡馬,而是但凡具足其中之一,即為惡馬。惡到什麼程度,難教難調難馴到什麼局面,單看具足幾種態勢,又囂張不拔到什麼地步?至於八態具足的,僅能說是惡中之惡、惡之翹楚、惡馬中的盜跖了!為如來勢必「殺之」的極惡之馬了!
最發人深省的是,所謂惡馬,不同於鈍馬、羸馬、駑馬,並不指涉外表身軀的羸質瘦形、或智能的遲緩愚鈍;相反地,卻可能膂力強健、壯碩華美、才具能力特出……使之成為惡馬的,全是心態、習氣、與情性──那份偏執的我見、我慢、我感,以是抵忤不服、爭諍、與反噬性。以是「人中龍鳳」或更有潛力成為「教中惡馬」,唯其具足更足以憍慢自恃的權勢、財富、聲名、才具……事實上,任何人,不分智、愚、賢、不肖,但凡我慢熾盛、好爭好諍、不調不裁均有大量潛力淪為惡馬。
人們並不願面對當面揭舉、出土的過失、過誤。「聞過則喜」是甚深難為的境界,泰半的人多半是聞過則怒,而隱覆、否認、迴避、推諉、拒絕認知或憶想……
凜白成癖,一己則是「聞過則抑鬱、沈痛」,下意識地痛毆自己,鉗鎚、責咎自身:「怎還有如此之病、如此之弊?」及至薰修「轉識成智」(即轉意識所及為智慧),把掌了「若於轉處不留情」──瞭然轉化之道,在於安住清明,不滲染情念、心緒,才漸行放捨痛毆、鞭韃的習氣,僅是等觀如幻,平定、安澄地調攝拔除。
沈鬱,固是一種情緒;連痛毆,也只是「頭上安頭」、更增重擔而已。拔刺便只是拔刺,不必更增添。
如斯於時光中將深重、深抹的沈鬱漸漸擦淡,僅是智照省察、平定而轉,不滲留情見、情染。
而所謂惡馬全出自之於過患被揭舉的「執慢」,而衍生出八類積極或消極的抗拒、反彈、反撲、和反噬;也全出於自保系統、自欺機制──然,不知過患,又如何談修行、調攝?以是「知煩惱,明過失」是修行的第一步。
準此,惡馬八態恰足以遮蔽眼目、積厚無明,形成修行的障阻與黑幕,緣於自既無能認知盲惑病灶,也不許人指陳。內、外無燈,俱不照明,結果,便只能瞎盲、瞎黑!
八態不剷,則也無從談修行、修善。
也許,我們所需的,並非更多更浩瀚華璨的名相、教典,而是回歸本質,把掌最根本、樸實、馬步性的幾則教法,烙印不忘,終其一生奉為軌轍,以為師鐸、為警醒、為操持──
「惡馬八態」即屬如是的教法:八條戒尺教導成為一名調馴的好佛弟子,不踢蹋、污塗佛座。
梵行者,不止須立志不成為如來惡馬,且誓願:
願為佛前一良駒!
寫于二〇二四年六月六日
(註一)軛,即駕置在車衡兩端、用以扼住牛、馬等頸項的曲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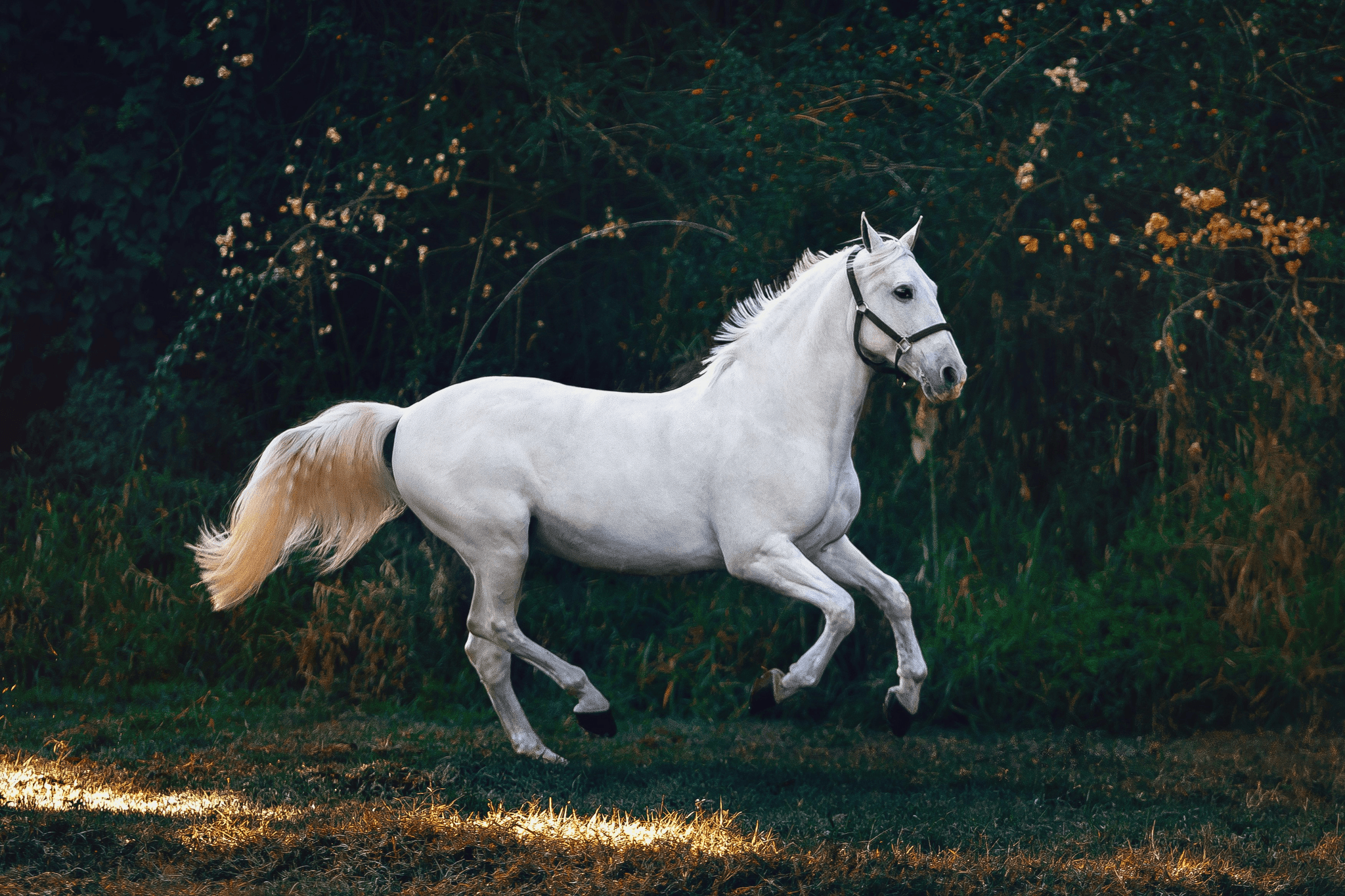
相關連結:

